
哪部作品的观众反响是最强烈的?
张瑜:我没有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,蛮可惜的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上海电影制片厂是我的一个归宿,是我的家。尽管一些老人都不在了,但是演员剧团那种氛围还在。对于中国电影整个历史长河来说,上海电影制片厂真的为电影做出了很多的贡献。我觉得蛮荣幸的,能够做一个改革开放的参与者,能叙述一些过去的事情给大家知道。
从《庐山恋》到《巴山夜雨》,再到《小街》和《知音》,《庐山恋》应该是观众反映最强的。《庐山恋》它不光是当时在放,包括后来在庐山电影院也一直在放,到现在为止,已经整整38年了,大家都很喜欢去看。而且特别是在金鸡奖百花奖的时候,大家都会很热情地去投入,去买《大众电影》杂志。

那时候,《大众电影》杂志的发行历史是巨高的,而且每一个老百姓都会为了这件事情非常投入地去填写,这个电影怎么怎么样,这种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。可见当时电影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之大,是他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去亲吻一个男孩子,那么一个吻也是让人家忘不了的,也改革开放“银幕第一吻”

最重要的,《庐山恋》是给人一种希望,给大家一种美好的感觉,还有穿泳衣、牛仔裤、花衬衣、连衣裙……我记得我的观众来信当中,很多信提及的就是,你的那件衣服是怎么做的,你的这些衣服是从哪儿买来的。所以我就说,它就像一股清晨一样的,让人们的眼光突然一亮,觉得还可以这样穿着,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去追求美,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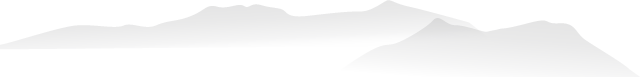
创作《巴山夜雨》的人物角色有难度吗?
张瑜:我觉得创造《小街》和《巴山夜雨》是有难度的。那么我觉得最难演的一场戏是什么呢,是在船舷上,我找不到了李志舆演的这个角色,秋石,我就到船舷上去找他,然后他和我之间的一番对话。这场戏什么也没有,可以借助的东西非常少,我的台词就说了一句,你,胡说,就这么两句。

整个过程实际上是演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,从刚开始拒绝,决然不能接受他的话,到慢慢地可以听进去,那我的眼神变化就慢慢地开始收敛。其实设计得还是蛮有意思的,而且我觉得整个船上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是让人揪心的,所以最后《巴山夜雨》是得到了一个金鸡奖集体的配角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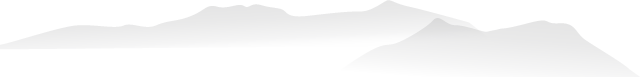
《小街》感触最深的创作过程是什么?
张瑜:在创作《小街》时,有意思的是无意当中产生了一些偶然,而偶然被人们记住了,不能忘怀,比如“张瑜头”。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这个角色的女扮男装,没有办法,才剪成了那样的一个短头发。导演带摄影师还有我,我们到了上海南京理发店,一个叫“小老虎”的师傅给我剪的。

当时这个理发师就觉得非常喜欢这个发型,他就把这个拍了张照片,把这个照片就挂在了照相馆的墙上。然后因为这部影片,很多姑娘们就想剪这个发型,但是又形容不出来,就指着这张照片说,我要这个发型,无心栽花柳成荫,就是这样子。

我觉得,可能最初的伤痕文学它更加暴露、更加直接,它讲的是知青经历的一些心里的苦难,但是当人们把这个负面情绪宣泄完之后,人们就进入了一个深层次的反思阶段。其实大家常常问我,你在你自己所演的这些影片当中,你最喜欢哪一部。我往往会说,《小街》是我的最爱,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影片,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共鸣的地方。

这个角色就像是一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,永远在胆战心惊中过日子,装扮成一个男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,还要裹胸。那段戏我演得非常忘我,我哭了很久,我不能停,停不下来。我会想到一个女孩子正在发育的时候,因为大环境所迫,她不得不掩饰住这些,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。
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比较典型的伤痕文学之后,再次反思的这么一个故事,希望人们重新找回自我、尊严、人性。我已经披上了长发,开始有了那种女性展现出美的那一面,咬到头发,头发飘动的那个状态。我们等于说直接从生活中走出来,就是这个样子,所保持的东西,比如他的纯真、质朴,这些东西都是抹不掉的,这些都真实地记录在银幕上了。

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有一些影片,演员在那哭得稀里哗啦的,但是你一点都不感动。为什么?我仔细研究过,我发现他只是在用技巧,但他的心没有因此而动。假如你身心不动的话,你怎么会塑造好一个角色,我不理解,我也不能接受。
我和陈冲一块演的戏,叫《青春》,我们当时也很年轻,我们都直接从学校出来就走上了银幕。但是我们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,我们演的是通信员,所以我们就要去接受训练,然后还要像通信兵一样去爬树干,都要亲自去体验,肩上磨得全是泡。

当时《大众电影》登了张瑜跟陈冲的一个摘录下来的往返的信,张瑜的回信特别有意思,就说我不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造卫星,演员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去塑造角色。当时我们的语言都是这样的,我记得很清楚,生活中的交流也都是谈工作,谈如何表演,每场戏演好,都是这些事情。
我记得我和建亚谈恋爱的过程就是书信来往,真的,拿出一封来都能公开的,全部是鼓励的话,卿卿我我的话很少,最多就是最后一句话,三个字。所以你会发现,一个时代它真是造就一种人、一种价值观,有时候这个可能还真是能影响一辈子。
我也因为这些戏,我很感谢电影,我不希望我被人们像放射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地放到天上去,我还想更接地气一点,认认真真、全身心地投入,这是我学到的一种敬业精神。
纪念改革开放40年最值得纪念的是什么?
张瑜:它的真,它和生活的紧密的联系。我可以这么讲,从改革开放初期,包括70年代末,整个电影是非常蓬勃、非常巅峰的,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,能够让我们唤起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,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。

就像在《小街》里面的一首歌,《妈妈留给我一首歌》,忧伤当中又带了一种美好。这首歌其实旋律并不复杂,但是它有妈妈这个形象,代表了尽管我们现在在经历这种苦难,但是未来是美好的,所以不要忧伤、不要悲哀,唱起它你心中就充满欢乐。

 80年代最红女星庐山恋影响一代人 留恋国外与丈夫离婚
80年代最红女星庐山恋影响一代人 留恋国外与丈夫离婚